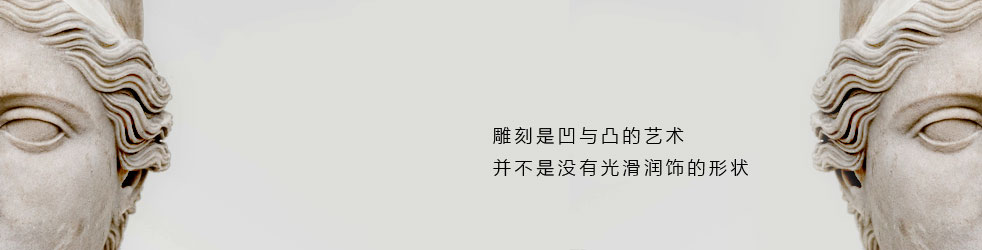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艺术与投资》:现在非常流行的“四川画派”这个概念和当年的“乡土”“伤痕”时候所讲的四川画派有很多的区别,更多的是一个市场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进入,可以怎样划分“四川画派”这庞大的群体呢?
叶永青:我觉得四川画派是一个早就应该超越的概念,不能局限在这样一个概念里面来谈它的前景、格局,因为四川画派是当年77、78级开创的一片天地,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延续下来,从四川出来的这批年轻艺术家会越来越弱化,不会超越以前的东西。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现实,今天的艺术家都走在自己的路上,不能总是用一个标准、框架来定位他们。在不同的创作情形下创作出不同的作品,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比较匮乏的年代,艺术家靠逐步积累、靠努力争取来获得现实里的各种权利和可能的资源进行创作。今天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面对的就是过剩的现实,就是靠删除,要对所有涌来的东西说“不”。
今天从四川出来的这么一批蔚为壮观的创作群体,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可以做一种观察——把他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种是50年代出生的,包括早期的四川画派的一些主将,还有“85新潮”以来的一些老艺术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都已经是市场上的红人;另外一拨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他们中的有些人实际上已经是现在四川画派的中坚力量;第三类就是70年代以后到80年代的一批被市场所推举的群体,他们一开始就非常商业化。市场上的表现,形成了一种两头翘、中间下垂的局面,这里面的原因很耐人寻味。
《艺术与投资》:这三个群体的艺术市场状态大致有什么表现和特征?
叶永青:50年代艺术家市场走高,这是自然形成的,也是历史形成的,刚好是跟市场、学术在生态上有很和谐的关系。以前80年代人人都热爱艺术,千千万万的人都走在艺术的路上,经过很多年的筛选和淘汰,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十来个人,自然地被社会吸纳、消化掉,包括他们的作品,在学术上的地位、在市场上的份额、在国内国外各种收藏的格局里都恰到好处。我把他们比做一碗“手擀面”,作品非常质朴,但又很好识别,可操作性强。今天如果你要操作这类艺术家的话可能投入比较高,但是回报同样也是很稳定的;60年代的这部分艺术家是创作能量最大,而且也是现在最努力的一批人,但是被夹在中间,是很尴尬的一个群体,但今天他们在所有艺术方面的活跃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我把后面70年代艺术家看作“速食面”,他们“一桶一桶”地被制造出来,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事情,不会犯错误。在人人都不会犯错误的时候,能否推举他们的就是看其背后的资金和利益集团的强大与否,能不能把他们放在生产链上,把他们推销、包装成一个名牌,70年代后的艺术家都很自然地进入了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市场不是人为能控制的,市场有市场本身的规律。比如一个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无论怎么去做他的东西,都不会贬值,很多人很早就在说这些人有泡沫了,但是你发现到100万的时候没有问题,200万没有问题,300万还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少。还有当年这些人在创作的时候没有市场一说,他们不是为市场画画。而现在我们这些“勤奋”的艺术家可能达到一年100张画,在当年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来画画,没有市场的刺激。他们画画就是为自己画,为一些展览分配会很自然,所以不会有我们今天所听说的那种危机和耸人听闻的事,而且那些作品都是大大小小的。但是今天的很多画家就变成像工业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商品一样。我们做一个假设,一个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哪一个能做到100万以上,100万一定是一个坎,这些画家都是画3米、5米的大画,一年100张。40万、50万没有问题,100万所有人都把画拿出来了,等到市场上开始大量出现艺术家100万的3米、5米大画的时候,这个艺术家怎么做,哪一个画廊能收拾这个残局,这些问题就是60年代要面临的问题。但70年代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是和画廊“合谋”。
《艺术与投资》:川美艺术家的成长和展览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开始比如是官方体制内的各种展览,到后来90年代的“青春残酷”展览,对那个时候部分的川美艺术家作了合适的度量,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川美艺术家参加国际大展成名,这些都似乎是在一个良性的、缓慢的过程中出现的。而近几年多了由画廊主导的展览,这些展览对老艺术家和年轻艺术家来说,各有怎么样的影响?
叶永青: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艺术家找一个方式来出场,像“青春残酷”或者别的也好,这只是一个命名。中国的每一代艺术家尤其是年轻一代艺术家他们在出来的时候遇到了最好的时机,得到了市场、世界对艺术的关注,这是好事情,但同时也把别的事情给遮蔽掉了,一个艺术家很快就衣食不愁。当代艺术的本质就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样的,强调一种实验性、可能性,它的基础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很大意义上是商业的结果。市场有需求,这种份额是挤压出来的,中国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发展出来的所谓当代艺术市场首先是由海外形成的,形成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概念和看法,这些概念会带来一些争论,形成了一种金字塔的模式,永远都是从塔尖上往下流失。随着中国一些人购买力变大,藏家来拿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这些艺术家从一开始卖不出去到供不应求,中国的一些画廊或者藏家拿不到这些炙手可热的艺术明星的作品时,那么他们就他退而求其次,开始制造自己的“方便面”。当然,每个画廊都做这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在学术上的一个思路是什么,跟时代的关系如何,在艺术语言上的说服力如何。画廊主导的展览无所谓好还是坏,还是看每个展览是怎么做的,什么样的展览,推出什么样的作品。每个展览都有区别。我觉得好多展览就是一个Party,连促销都算不上。
《艺术与投资》: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忽略川美画派的成长和策展人之间的关系。90年代后成名的艺术家也得益于策展人所策划的重要展览,这就绕过了以前官方展览的渠道。策展人策划的展览对艺术家有度量作用,但不一定都能起到好的效果,尽管新一代的“卡通”定位遭到质疑,但又不可否认地影响到川美在校学生的“卡通创作”。
叶永青:“卡通”只是一种资源,一个人用不用“卡通”是他自己的事,就像过去的一个艺术家采不采用政治的符号一样,这是他对时代的一种感觉。中国70年代后出生的这些人真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在整个近代史里,中国从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太平盛世,他们是真正赶上全球化的一代。我的女儿也学艺术,她去年参加上海双年展,我做上海的“Moca”展览,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对他们帮助很少,基本上我们各自走在不同的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东西。
《艺术与投资》:这是否与川美的传统有关?
叶永青:川美确实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有一种大家都很努力的良好风气。川美主打的都是架上的绘画,这主观上会让一些画廊觉得这里面有机会;还有川美许多艺术家画的品相比较正,容易被市场接受,但价格不一定等于真正的创造力。四川人头脑比较活,容易调整,四川人之间互相有一种氛围,我以前一直就想做一个展览叫做“身边的气息”,他们不是靠着对历史的领悟、文化上的判断力,他们甚至很本能地靠闻着身边人的味道就可以生存。大家的竞争是那种短兵相接的、非常较劲的竞争,你卖一张画,我要卖两张画。画廊最早来四川美院是9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们都还很穷,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当时我跟张晓刚还在重庆,何森、陈文波、忻海洲他们都散居在重庆的各个地方。画廊、收藏家、批评家不管是来看我也好,看张晓刚也好,我们都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让他们还能看到其他人的优秀作品。后来何森、赵能智、陈文波等等,大家都自觉地在黄桷坪周围租房,这就形成了现在所谓的“黄漂”的一个雏形。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形成的样板,其实就是每一个艺术家生活、创作的模式,是互相之间的影响造成这样的东西,大家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长本事,学到新的东西。
《艺术与投资》:对于年轻的川美艺术家来说,特别是刚来北京不久的年轻艺术家,川美庞大的人际资源无形是给他们许多便利,那他们目前最大的困难又在哪呢?
叶永青:困难就是能否找到适合他们干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要靠出卖自己的艺术为生。我没法回答一个人怎么样利用艺术来建立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这是运气或机遇的问题,但每个人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要做艺术,如果真的做这个不开心,那就可以换别的行业。
《艺术与投资》:我想提一下“川美”这个创作群体里的另一部分人,就是那些不是市场炒点的做装置和影像等等其他非架上媒介的艺术家。基金会对于他们来说目前显得要更为重要,他们的收入渠道要比做架上的艺术家窄,特别是留守重庆的艺术家。您觉得基金会目前能介入到这个市场中来,给那些身处资源匮乏地区的艺术家提供帮助有哪些可行条件和制约因素?
叶永青:每个基金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大多数基金会都是非盈利的,可以帮助艺术家提供一些条件,但不负责把艺术家推到市场,基金会也不操作市场。在西方有一些艺术家是终生都没有进入市场的,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做展览,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的办法就是去基金会申请到创作经费和到世界各地进行创作的条件。这些是西方的机制能提供的。我们中国目前来说从“昆明创库”到现在,北京很多人在做盈利空间和非盈利空间的可能性中不断尝试。从川美本身来说,恰恰就是看起来人才济济,但其实是在价值观上比较单调的一个创作群体。衡量这个创作群体的标准比较原始,就是参照身边的成功范例作为标杆,独立性相对较少。
《艺术与投资》:艺术园区是近几年来各地都热衷的话题,川美所在的黄桷坪街也建起了艺术一条街,但仍然无法与自然形成的798、莫干山路相比,总的来说就是生产力不足,关键还是吸引力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川美是原材料基地,加工都在北京、上海,这种过度集中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会拉大四川、重庆和北京、上海艺术资源的贫富差距吗?
叶永青: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心城市的兴起必然是以别的城市的衰落为代价的,非洲种出咖啡豆,跟星巴克里卖的咖啡是两回事。四川出来的这批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全球化和今天这样一个大的格局里面,这些艺术家以后也不会把自己局限为四川画派的一员。我想没有艺术家会这样去包装自己,但是因为商家或者画廊有这样的诉求去诱导消费者,无非是因为这里面产生了一些名牌和一些经济上的效益。
《艺术与投资》:我记得您策划过“贵阳双年展”,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四个西南城市参与进来,这些城市的资源相对少一些,您觉得它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叶永青:世界上所有被强势的文化或强势的城市压抑的地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反弹,这些反弹往往都会发生在经济上、文化上或者在艺术上弱势的城市。全世界最需要双年展的是什么地方,绝对不是纽约,不是东京,也不是巴黎,一定是二级城市或者叫在文化上的二手城市,重庆就是一个二手城市,成都也是,他们永远都在吃别人吃剩下的东西。但不代表这些城市没有创造力,不代表它们没有自己文化的性格和激情,但它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创造属于它们自己能够玩的模式,而不是跟在上海和北京后面亦步亦趋。
发表评论
请登录